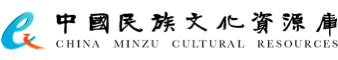

牧场,是个神奇的世界。它在初春时变绿,迎来牛羊,喂养它们,同时也给牧民以殷实的生活。牧场一年绿一次,年复一年,渐渐绿出了生命和精神的伟大。它用自己的生命喂养了更多的生命,印证着万物互相依赖的伟大原则。同时,它也孕育出了恒久不变的游牧精神。
燃烧的牧道
每年5月,牧民们赶着牛羊进入牧场。牧场离村庄或远或近,近的一两天就可到达,远的则要走十几天。上路的那天,牧民们将牛羊归拢到一起,沿山道缓缓行进。不一会儿,灰尘便被牛羊踩起,在山谷中一团团弥漫,使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到了牧场,人们选有水有草的地方扎下帐篷。水与草是先祖们在多年前选择生存地时的必要条件。水,可以供人畜饮用;草,可以供牛羊啃食。这时候,牧民们各自选一个地方将牛羊分开,让它们在山野里去吃草。今年的草已经全部长出,牛羊们开始了又一次盛宴。
放牧的日子,人与羊在山野里相处得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野事野趣。有一次,一场大雪提前降下,将草全部埋去,羊饿得不行,便选一个陡坡向下跑,快到树跟前了猛地腾起,用嘴咬住或用两个前蹄夹住一根树枝,“啪”的一声,折断的树枝和羊一起摔在地上。羊们扑过来抢吃树叶,头碰在一起,地上的雪被踢得乱飞。羊饿急了都会想出这样的办法。还有一次,一场大雪把几只羊冻坏了,牧民们无法把它们带回,只好将它们宰掉。这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果不把它们宰掉,在人走了之后,狼就会闻着它们身上的膻味围拢来将它们咬死。羊落入狼嘴是牧民的耻辱,谁也不想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返回时,牧民们生起一堆火,让羊烤暖和站起来,才动了刀子。牧民们认为羊的腿是尊贵的,走了那么长的路,爬过了许多高山,所以必须得让它们站着死。
到了秋天,便是返回的日子。人们又像来时一样将牛羊收拢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集群。不会有人担心牛羊会混淆,牧民们的眼力都非常好,他们会像认自己的孩子一样一眼就可以认出自家的牛羊。返回的路途依然热闹无比,牛羊们涌入山谷,很快便又踩起灰尘。灰尘慢慢向上升腾,将牛羊映衬得如同滚动的石头。骑马的牧民这时在牛羊群中散开,指挥着牛羊前行。有人曾在远处见过牛羊们走过山坡时的情景,它们将整个山坡占据,升腾的灰尘在夕光中如同正在燃烧的火焰。
但你仔细看一看那些牛羊,它们都一一低着头,只管静静地向前走,不向任何地方张望。牛羊有灵性,一上路就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只顾安静地走路。羊的路在心里。羊低着头走路,头几乎挨着大地。羊多像一个个听话的孩子。

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孩子,早早地融入了游牧世界
那仁牧场
“那仁”这个名字起得好。那仁,是新疆人经常吃的一种面。将面条盛在一个盆子里,再放上羊肉和葱,吃起来颇为爽口。这种饭在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家里很常见,喝完酒后吃上一些那仁,身心顿时舒服无比。我曾在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家吃过一次那仁。他的回族妻子先将水烧开,飞快地拉面。锅中的汤翻滚沸腾,从她手中拉出的面条飞落入锅中,看着让人心欢。那顿饭吃得可口,现在每每想起,仍让人觉得那股香味犹在唇边。
每年有十几万头牛羊进入阿尔泰山深处的那仁牧场,像石头一样散散乱乱分布在草滩、山坡和河道上。有人骑马在草地上奔驰,引得牛羊抬起头凝望,片刻之后便又低下头去吃草。每天早晨,牛羊们也许是被明媚的阳光感染,不时地发出欢快的叫声。羊有时候很像人,有时候两只长着同样角的羊走到一起,盯着对方看一会儿,便去斗。斗羊是刺激的事情,很快就引得旁边的羊来看,两只羊谁也不服谁,狠狠地用角撞向对方,碰得“啪啪”闷响。有时候,由于它们用力过猛,将角也碰掉了。羊斗起来会没完没了,把吃草忘得一干二净。主人发现后,会骑马过来把它们喝开。两只羊不情愿分开,狠狠地盯着对方。如果它们以后又碰到一起,还会斗一场,对方的样子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心里。除了羊,人也会在那仁经常弄出些热闹的事情。有一年,一位牧民发现有兔子到草滩上吃草,他着急地对着兔子大喊一声“干什么”。兔子被他的声音吓得蹿入了树林。他心疼草地上的草,兔子把草吃了,羊吃什么呢?第二天,他将牛羊赶出去的时候,就对树林子吆喝一声“干什么”。也许兔子都被他的喊叫吓住了,再也没有出来一只。这些年人们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都要叫几声。其实,兔子进入牧场也吃不了多少草,甚至可以说,兔子吃的草比起羊吃的草微乎其微,但牧民们却很认真,哪怕就是一口草,也要让羊吃。
人在牧场上慢慢地便也变得质朴起来。一位老太太每天都坐在帐篷前望着牧场上的牛羊,一坐就是一天。人们都出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坐在那里,与帐篷一起组成了牧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谁也不知道她在凝望什么,反正她在那儿一坐就是一天。人们骑马走得远了,感觉仍在她目光的注视中,一丝温暖便泛上心头,下午走过她的帐篷前,人们都要向她点头致意。骑马回来的人不管跑得多快,都要在她面前下马,牵着马走回自己的帐篷。
一群又一群羊就这样在牧场上长大,长壮实,繁衍出下一代。羊的繁衍是不动声色的,很快,一个牧民就会拥有一大群羊。牧民们都很平静,春天把羊赶到牧场,秋天又赶回去。草场是大地的怀抱,草是上天赐予的,羊就这样在平静和从容中被喂养着,变成了大自然的孩子。
牧场在初春变绿,迎来牛羊,喂养它们,同时也给牧民以殷实的生活。牧场一年绿一次,却绿出了生命的伟大意义。它用自己的生命喂养了更多的生命,印证着万物互相依赖的伟大原则。
从表面看上去,牧场是多么美啊!一片绿油油,一直漫延向远处,不论多么高的山,多么深的山谷,都不能阻挡绿色前行的脚步。它们每向前迈动一步,就留下一根草,让它扎根、生枝长叶。
我想,这就是大地的青春吧。

牧场一角
羊咬羊的故事
下雨的日子,牛羊出去吃草,人留下来在帐篷里喝酒、聊天,聊一些以前在牧场发生的事情。
在一个雨夜,人们给我讲了一个羊吃羊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有一只羊,长得肥硕壮实,主人很是喜欢它,叫它“一百块”。在牧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只羊值多少钱,被称之为“一百块”的这只羊,羊角值5块,皮子值30块,肉值65块。在那个年代,100块钱是个大数字,所以那只羊就像村子里的能人一样很有地位。后来有一天,它突然在草地上打滚,四条腿不停地抖动。羊群正在吃草,被它的举动吓得四散而去。当时所有的牧民都在别的地方,所以没有人看见它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过了一会儿,它从地上爬起,向河边跑去。羊纷纷给它让道,它跑到河边跳入水中,但四条腿还是不停地发抖。它又从河中冲出,跑到一只羊跟前狠狠地咬了它一口,那只羊嘶鸣一声跑向别处去了。奇怪的是,它居然不再抖了。它摇摇头,感到浑身舒坦了,便又去吃草。但在第二天的同一时刻,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于是它又打滚、发抖、奔跑。后来它似乎记起了前一天的办法,就又冲到一只羊跟前,狠狠咬了那只羊一口,咬完之后果然又好了。
这样的事情在每天的那个时刻准时出现,那只羊养成了习惯,每次都选一只羊咬一口,才能止住痛苦的抖动。终于有一天,一位牧民看见了它的行为,大惊失色,回去告诉了人们。人们开始议论这只羊。有人说这只羊中邪了,得除去它,否则它会给牧场带来灾难;也有人说这只羊已经变成了狼,不然,它为什么要咬羊呢?幸亏被咬的那只羊跑得快,否则就被吃掉了。
不久,人们就将它的行为告诉了它的主人。那位牧民听了后大吃一惊,羊吃羊的事情多少年来在牧场上从未发生过,现在大家议论纷纷,他感到责任重大,于是便决定仔细去看看,看它到底怎样去吃别的羊。他不相信一只羊能去吃另一只羊,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吃另一个人一样。第二天,他藏在一块石头后面,到了那只羊每天发作的时候,它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开始打滚、发抖,并很快狠狠地去咬另一只羊。他气极了,好一个残忍的家伙,果真与人们说的一模一样。他从腰带上抽出“皮夹克”(刀子),冲上去将它一刀刺死。它尽管值100块,但它如果一天咬死一只羊,没几天他就赔惨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它宰掉了。事后,他突然想看看那只羊到底是为何要去咬别的羊的,他弄开它的嘴一看,顿时被惊呆了,羊的满口牙都有洞……他默默地把它的嘴合上,扛起它到后山埋了。他没有给任何人讲那只羊是因为虫蛀牙疼痛难忍,才去咬别的羊的。但因为他没有向人们说什么,后来的事情便发生了微妙的反应,牧民们由怀疑那只羊开始,继而又开始怀疑他。慢慢地把羊群和他的羊隔开,到了最后便不与他来往了。他很生气,我把一只100块的羊都宰掉了,而你们却如此对待我。但他还是不向人们解释什么,在一个黑夜赶着他的羊去了另一个地方,从此以后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
几年后的一天,村子里有一个人突然牙疼。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便在地上打滚。那个牧民走到他跟前,伸出胳膊说,“你咬我一下就好了”。那个人不明白他为何要那样,犹豫着没咬,他大声说,“快咬,肯定能行。”那个人就咬了,果然不再疼了。事后,那个人要谢他,他指着被咬肿的那个地方说,“没事,你能把我咬肿,我很高兴。”说完,他高兴地笑了起来,人们都不明白他为何那么高兴。
现在想想,人们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故事的谜底早已被揭开。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真实,不是什么传说一类的东西,一只羊的蛀牙是可信的,牙疼起来后去咬什么东西,使之麻木也是可信的。那个牧民因为将一只无辜的羊宰掉而保持了沉默,甚至甘愿受人们不公平的待遇,实际上是怀有负罪心理的。这一切也都是真实的。正因为一切都很真实,方使我感到沉重。不知怎么的,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我每天在牧场上走动时,碰见一只羊就心里一紧,感觉到它正在吃着鲜嫩的草的时候,蛀牙就会使它疼痛难忍。
碰到一个牧民,我便又忍不住想,不知他在生活中忍受了多少不被外人所知的事情?

夜遇阿克哈巴河
怎么说呢,看到阿克哈巴河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不是一条河。
天已经黑了好一会儿了,夜幕完全拉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挂在天边的月亮。新疆的地大,所以,经常能看见天上一边挂着太阳,一边挂着月亮。在白天,月亮只能悄悄地在天上挂着,不会被轻易发现,而一旦太阳落山,天刚麻麻黑,你总能看见远处的天边先亮了起来。不一会儿,那片光亮越来越大,一直涌到你的眼前。
阿克哈巴河也是从上游被一片月光照白,即而又慢慢向下,顺着河道在移动。我看到在月光的移动中,河水变得更白了;由于月光在动,河水似乎也在向下汹涌,这种汹涌是一团白光的涌动,越来越快,似乎已经倾泻起来。月光顺着河道从我面前移动过去。在越过我的时候,我看见河水的内层被照亮,很深,也很厚重。月光移动过去之后,河面只有一层淡淡的亮光,让人觉得阿克哈巴河仍不是一条河,而是别的什么。
这时候,一位哈萨克族牧民骑着马一边往这边走,一边唱着歌。空旷的夜晚因为突然有了他的歌声,一下子便被打破了宁静和孤独。他走到我跟前,从马上跳下来,愣愣地望着月光中的阿克哈巴河。我觉得他有点奇怪,怎么突然瞅着阿克哈巴河就发起了呆。过了一会儿,他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下,然后转过身去,准备牵马离去。
“哎,佳克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和他说几句话,就使用了用来称谓朋友的这句哈萨克语,叫了他一声。他听到我的叫声后停了下来,准备去牵马的那只手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了回去。他走到我跟前,也像我一样说了一句:“哎,佳克斯。”
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临河而立,望着月光中的阿克哈巴河,长久地沉默着。此时的阿克哈巴河面仍旧是一片铁青;我仍然感觉不到它是一条河。但在一扭头间,我发现他的右手上有血。再仔细一看,他的那只手正在流血,一滴一滴的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滴在了沙土中。此时月光正亮,因而他的那只手掌看上去黑乎乎的,可以肯定已经有大量的血流了出来。
“你的手……”
他把手伸到我跟前。我看见他的手心扎着一根像筷子那么粗的骆驼刺。他把手翻过来,我触目惊心地发现那根骆驼刺刺穿了他的掌心,在手背露出二三寸的一截。我知道紧挨着阿克哈巴河的山坡上到处都长着骆驼刺,骆驼刺较之于其它沙漠植物,似乎有着钢铁铸就的枝叶;其枝坚硬无比,其叶锋利如刃,人和动物一旦碰到骆驼刺上,必然会被划破皮肤;如果碰得重了,则会被刺入肉中。
“你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的马看见阿克哈巴河被月光照亮,就狂跑起来,我不小心跌落在地上,这根骆驼刺就钻到了我手心。”
“疼不疼?”
“有一点点。”
我扭头去看犯下错误的那匹马,它仍然在出神地望着阿克哈巴河。看它的样子,它很想向着阿克哈巴河一跃而入,但拴在它脖子上的那根缰绳却被它的主人紧紧地抓在手中。
“我本来想在河水中把手上的血洗掉,但一看见阿克哈巴河,我发现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它在月光中会是这样。我不洗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两腿用力一夹马腹,那匹马就奔腾向远处。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他的歌声。我知道,此时他跟刚才来到阿克哈巴河边时一样,正高声唱着歌。而那些鲜血伴着歌声,正从他的指缝里一滴一滴地落入沙漠。
文章写到这里,我才记起,当时他面部的颜色和阿克哈巴河一样,都是铁青色的。

转场
奔跑的牛
人们在牧区谈论的这一头牛比较普通,在牛群中,毫无特征可辨。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天它突然奔跑起来追一只狐狸,也许牧民们永远都不会关注它。那天,所有的牛羊都在安安静静地吃草,牧民们坐在帐篷门口懒懒地晒太阳。突然,有人高呼一声,快看,那头牛干啥哩?众人看过去,见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头牛在追一只红狐狸,有石堆和杂草不时出现在它蹄下,但它却并不躲避,只是飞快地从上面一跃而过,继续向前奔跑。
“是艾尔肯的牛。”
“不是,是格尔林的。”
“更不对,是索林多的。”
牧民们争论不已,但都不能断定它是谁的牛。那个山坡离他们有几百米远,他们只能看见是一头牛在奔跑,无法断定它到底是谁的牛。它跑下山坡后,人们才看清它是格尔林的。
那只狐狸有红色的尾巴,或者说全身都是红的,跑起来红光一闪一闪,像是有一团火在山坡上滚动。那头牛紧紧地盯着它,不管它跑到哪里都死死不放。牛是大物,跑动时四蹄踩出很大的声响,狐狸疑心它始终就在自己身后,只顾逃跑,连回头张望一下都不敢。也许,它根本不知道是一头牛在跟自己过意不去。
牧民们看得高兴,一头牛和一只狐狸,这两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动物,今天居然碰在了一起。不知道牛为什么要追它?也许,它吃了牛刚要去吃的一株嫩草;也许,牛卧在什么地方刚要打个盹,是它经过的脚步声惊醒了牛,牛很生气,便要捉住它问罪。狐狸聪明至极,一看情况不妙便跳起身就跑。狐狸以前肯定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见身后的那个家伙追个没完,便只有拼命往前跑。
牧民们一边看热闹,一边议论,要是这头牛追上狐狸,一蹄子就可以把它踩死,狐狸皮是好东西,能卖不少钱呢!格尔林这两天不在牧场,如果他回来,就不要告诉他那只狐狸是他的牛踩死的,等狐狸皮卖出去后,大家分钱,凡在场的人都有一份。但事情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情景,那只狐狸跑到一片草丛跟前红光一闪,顿时没有了踪影。牛失去了追逐目标,在草丛四周着急地打转,却再也找不到那只狐狸。牧民们觉得那只狐狸可能在草丛中躲了起来,便跑过去围堵,但他们把那片草丛翻了个遍,也不见那只狐狸的影子。他们又怀疑它钻入洞穴了,掀开草皮找了一遍,还是没有。他们觉得,狐狸可能会什么变身术,见自己实在跑不过身后的庞然大物,就摇身一变遁去。
牧民们怏怏而归,他们一转身,才发现那头牛不在了。不知什么时候,它已经走了。

高处的窗口
快要转场了,我走到牧场东边的山坡顶,坐在一块石头上鸟瞰那仁牧场。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牧场的全部——所有的牛羊、树、一条河,以及帐篷、羊圈等等,都尽收眼底。在场上不会看到它的全部,而现在却全部看到了。这个山坡顶是那仁牧场在高处的一个窗口。
看着看着,我便觉得那仁牧场像一个人,在这些天来,我站在它的对面,目睹着它从头至尾完完整整地经历了一件事。是的,在牧场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相对于牧场而言,其实就是一件事。牧场像一个历经了沧桑岁月的老人一样,随心所欲地让一个季节只发生一件事。从头至尾,它都很从容,似乎早已在内心知道事情将怎样发生,又将怎样结束。牧民们也同样有这种心态,在整整一个季节里都显得不慌不忙。多么好啊,让人觉得在牧场上经历一个季节,便犹如度过了一生。如果你这样走到暮年,然后回头张望,你便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其实只是一件事,多少年了,事一直如此持续着,而且经久弥坚。
我想,对于牧场来说,不论是一个季节,还是一年,或者一生一世,再抑或永久,都只能发生一件事情。它在开始的时候就已进入永恒,所以,它从此便再也没有开始或结束。
这种持之以恒,并一成不变的东西应该被称之为什么呢?
在牧场的另一个山坡上出现的景象马上使我茅塞顿开——一群提前转场的牛羊列成一个长队,正缓缓从山坡上走过;而我在第一眼看见它们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一个词:游牧。
在牧场,我看到了延续千年的游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