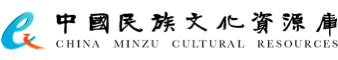

在黔东南州苗族民间几个不同次方言区的传说和理念中,都认为“蝴蝶妈妈”和蝴蝶诞生了人类
在研究苗族的蝴蝶图腾现象中,不少人感到困惑,据说主要是在今天的生活中找不到蝴蝶崇拜的依据。又据说,就连将苗语Mangx Bangx Mais Lief(妹榜妹留)首译为“蝴蝶妈妈”的今旦老先生当初也觉得没有把握,为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李炳泽先生也质疑,他还认为可以翻译为“名字叫做Bangx Lief的妈妈”。吴晓东先生的《苗族图腾与神话》直接认为蝴蝶不是苗族的图腾,以为“苗族没有可靠的蝴蝶崇拜习俗”;“苗族蝴蝶生人母题为后期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否受到华夏族蝴蝶变人传说的影响,也说不定。《庄子》里有庄周化蝶之梦......”等等。
我童年时便有过切身的体验。祖母每年都养蚕,当她不知从哪儿将细得像针一样无法分辨的蚕幼虫弄来时,很庄重地告诉我,这是从天上榜榴妈妈(蝴蝶妈妈)那儿抱来的。蚕的幼虫被放在一个小竹篾盛器上用炭火烤,火盆里盖上一层薄灰以保恒温。祖母说,天上的蛋请脊宇鸟孵抱,地上的蛋请火炕孵抱。待幼虫渐渐长大了,再移到一个大簸箕里。最后,祖母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弄出许多旧门板、宽木板,将蚕们移上去吐丝。蚕们在板上织完一张蚕丝单,就用最后的丝将自己包裹起来,完成“作茧自缚”。我以为那该是蚕的棺材,祖母告诉我,那不是棺材,是她们的变身房。祖母把蚕蛹拢集到桑树下,果然,蛹们化作无数飞蛾。那些美丽的天使是千万碰不得的,用手去触摸,手指就会腐烂。这是祖母的警告。还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得称她们为姑娘,去外面要蚕回家,得说“娶”,送出去又得说“嫁”,一切针对蚕的言行都得拟人化。
我近期在重读几个版本的《苗族古歌》时,这些景象总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由田兵编选于197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古歌》版本,是一个文字较为规范的文本,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又出自名家之手,自然影响深远,不少学者都习惯以其为鉴。但其与原来的蓝本,即1958年由贵州省作家协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相对照,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又显得太汉化,使今天的研究者们丧失了许多当时己搜集到的信息。现在研究苗学的专家们大都在出版物上读《苗族古歌》,搜集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资料,十分珍贵,原初第一手整理的资料,都出自当时民间的原唱者。那时他(她)们大多已50岁以上,如今已经离去。由于苗汉语言之间的差异,尽管那些句式结构、那些看似逻辑混乱的意象,都可能含有重要的信息。
苗族的祖先为什么要选择卵生的生命形式作为人类的生命形式?我相信,即使是创造了这一神话的祖先们也已经清楚了人类是胎生而非卵生。你看,这一卵生程序如此麻烦:蝴蝶要去和水泡恋爱,才生蛋,生出了蛋又不能孵化,又去请脊宇鸟来孵抱。我们推想,处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和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中的人们,不会像当代人这般在丰衣足食、闲遐无聊之际刻意去寻找诗意灵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着生存大计,也许每天都面对死亡。这些迫使他们去思考,迫使他们从周围世界中认识事物,以它们为参照,寻找自救自强的真谛。
自人类学会思考,对生命的关怀就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生命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在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以至多少代人的观察后,他们发现了蚕蛾科昆虫生命历程的奇迹:蝶生卵——卵成虫——虫变蛹——蛹化蝶。现在的科学称为完全变态昆虫,而当时的人们却以为这是一个神奇的再生过程。人类如果能获得这样的生命程式,人的生命就会不断地轮回再生,人的生命将获得永生。于是,对蝴蝶这一卵生的生命形式的崇拜产生了。那么,人也只有选择蝴蝶作为人类的母亲,才能获得像它那样的轮回再生。
在搜集于黔东南不同地区的苗族古歌版本里,都综合表现了先民们这一原始的理念。田兵选编的《苗族古歌》“十二个蛋”里,多用唐春芳搜集的材料,而另一个由桂舟人、赵钟海搜集的材料没有用,那里有这样的句子:“蝴蝶生蚕虫蛋,团鱼生岩石蛋⋯⋯蝴蝶生下蚕虫蛋,送给火炕三捆柴,火炕才来抱”;《苗族史诗·十二个蛋》也说:“来看十二个蛋吧,看那古老的圆宝。蛾儿生蚕蛋,蛾儿生了它不抱,让绐谁来抱?蛾儿生蚕蛋,生在构皮纸上,交绐火炕抱”;燕宝的《苗族古歌·十二个蛋》也说:“蚕儿生蛋蚕不孵,让绐谁来替它孵?蚕儿生蛋蚕不孵,让给簸箕替它孵”;吴德坤、吴德杰的《苗族理辞·蝴蝶产卵》中又讲到了另一种新信息:是蜻蜓和水泡沫相交,产卵在河沙滩上,得到老鹰的忠告,才移到悬崖上去孵抱。
不要以为这些是一组很混乱的事象,我们也曾经质疑过那些传歌的老人:这个说是蝴蝶,那个说是蚕,那个又说是蜻蜓。到底是什么?传歌者总是笑而不答或说怎么唱都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要去管它是蝴蝶、蛾儿、蚕还是蜻蜓,这一切都为着叙述卵生这一生命形式。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黔东南苗语里,蚕的飞蛾和蝴蝶是同一样的称谓:“Bangx Lief”(榜留),也就是说都统称为蝴蝶。
苗族先民们把枫木、蝴蝶、脊宇鸟组成一曲完美的人类生命乐章:枫木被砍倒了,然而被砍倒的枫木并没有死——树根变成泥鳅,树桩变铜鼓,树疙瘩变成猫头鹰,树叶变燕子,树梢变脊宇鸟,树心生出蝴蝶;随后蝴蝶就与水泡恋爱,生出十二个蛋,再请脊宇鸟孵化出人类和数种动物。在这曲生命乐章中,本来鸟就可以独立完成生蛋和孵化全过程的,但鸟类没有那种不断变化生存方式而不死的生命程式,这才是生命的主旋律。而鸟类的保护又不可替代,鸟是祖先的图腾。
猜想:以苗族的蝴蝶妈妈为代表的卵生图腾崇拜才是丝绸的主要起源
正是苗族先民们对蚕从卵到蛹再化作蛾的生命变态过程充满了好奇,由好奇到崇拜图腾。先民们希望死后用丝绸把自己裹起来,希望像蚕一样变化升天。蚕成了升向另一个世界的神通。但是,人的身体和蚕有巨大的差异,于是人们便想尽办法用蚕丝来为自己织一件裹身之布。这样,人工养蚕业和蚕文化就开始了。
史学历来持“丝绸起源于实用目的”之说。但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以苗族的蝴蝶妈妈为代表的卵生图腾崇拜才是丝绸的主要起源。最近,中国丝绸博物馆学者赵丰也提出了“原始先民崇拜桑蚕这一文化背景,才是我国丝绸起源的主要原因”的理论。他还认为,东南亚、欧洲等国也很早就有了野蚕,但都没有把野蚕丝织成丝绸,只有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把野蚕丝织成了丝绸。这是由于我国原始先民崇拜桑蚕的独特文化结果。
利用野蚕吐出的丝进行纺织,是人类利用自然的一项重大发明,丝绸在古代是中国特有的纺织原料。有人将全世界使用的纺织原料划分为四个地区:南亚地区是使用棉纤维,包括木棉和草棉;地中海地区使用亚麻与羊毛;而美洲则是使用棉花和羊毛;只有中国古代的先民因图腾而创造了灿烂的丝绸制品,苗族便是最早因图腾而注意到蚕丝的这种自然现象,并且天才地将它纺织成绢帛。苗族先民是我国蚕业和蚕文化的发明创造者之一。典籍上也记载了蚩尤部落是发明和饲养蚕的,《绎史》卷五说:“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絍之功。”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时候,黄帝战胜了蚩尤以后,蚩尤部落里的蚕神向黄帝献蚕丝技能,从而使中国有了蚕丝的使用。
我们来说说这个蛮字。历代都称以苗族为首的南方少数民族为“南蛮”,蛮字被文字简化失了形,看不出造字的本意,繁体字写作“蠻”,这里就看出与丝和虫的联系了。商代甲骨文已有“蛮方”。商末周原甲骨文有“庶蛮”。王宇信《西周甲骨文探论》说:“庶蛮即众蛮,或群蛮。如《春秋会要》载有‘群蛮’”。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苗蛮总察里说:“古代南方中国人原本一律称自己做蛮。蛮本来不从虫的,古时南方有语言而无字,蛮字也不过是中原的人把这些南方部落译音而已。从言,表示南方有语言。从糸,表示南方发明蚕织之术。然而因言是译音,所以有蛮、氓、蒙、闽、苗、麻、慢、蔓、满、瞒、孟、猛、毛等种种的互译。”直至今天,苗族仍以“蒙”自称。
汉代以后,蛮字加了虫底,大部分专家认为这是汉代对蛮人的歧视。我觉得尚值得推敲。上古时,才开始驯养的野蚕主要放在桑林里就地设架,把野蚕放框架内,让它围着框架吐丝。到了夏以后,居住条件有了改善,人们开始把野蚕移入室内饲养,逐渐变成家蚕。商代殷墟出土就有玉蚕可证。汉代开始,丝绸织造进入辉煌时期,此时,丝绸开始走出国门,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带去了大量丝绸,开拓了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后来,吴国又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与日本、越南、罗马贸易往来,日本的“和服”因此叫“吴服”。蛮字的涵义与古蜀人和蚕丛氏有关连,古蜀人是养蚕中的重要一支。《淮南之说林训》说:“蜎蜎虫蜀貌,虫蜀即蜀也”。《尔雅释虫》注曰“大虫如指似蚕”。在蚕桑文化空前发达的背景下,蛮字加虫底,或许是为了更加突出蚕的特性和家蚕的专业特性。

在史册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有关蚩尤部落的后裔桑蚕业的记载
当丝绸在世界面前一片辉煌的时刻,曾经创造了丝绸文化之源的蚩尤部落、苗族在哪里?蚕神随着部落的战败而把这一创造发明贡献给了黄帝的华夏,然后又变成了黄帝螺祖的专利。历史再也没有赐给他们再续丝绸辉煌的机会,但这并不能说苗族再也不发展蚕桑业了。
《史记·夏本纪》说:“莱夷为牧,其篚盒丝。”莱夷又称“仡莱”,是东夷融入三苗部落的一支。苗族曾经是楚国的主体国民,在楚国的中心地湖北、湖南,是我国古代丝绸发展的重要基地,众多的出土文物见证了一切:1982年,湖北的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了一大批丝绸织品,绣绢、绣罗、麻鞋、丝绢画,以及著名的蝉翼轻纱,震惊海内外。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了用以裹尸的5种不同纹饰的锦残片,这无疑是蝴蝶图腾的文化传承。而长沙马王堆出土丝织物更是精美无比,代表了同时代丝织生产工艺的最高水平。容观琼先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主软侯利仓很可能是“西汉以前苗族的部落首领”。
苗族古歌唱道:“麻栗和化香,栽山顶崖脚。”麻栗就是栎树,也叫柞树,专用其叶来养蚕的。古歌中说苗族西迁来时,带来九种树种,其中就有栎树种。据吴一文先生《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一书考据:“苗族看重栎树,苗族巫师占卦用的卦木,非五倍木即栎木,或双木并用,不能舍此二种而其他。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特别是养蚕方式的改变,人们已经淡化栎树镇邪的作用。可以肯定,栎树在历史上必定对苗族的社会产生过极大作用,以致它威力巨大,超过了支天的五倍木,成为专镇凶恶魔之木”。
亳无疑问,蝴蝶图腾即是对蚕的崇拜,蚕文化原初的核心便是人归途的仪式,人要在这种和蚕一祥的仪式中得到再生。今天的苗族,仍然保持着以丝绸裹身而葬的丧葬习俗。我祖母养蚕织就的丝织品,我们习惯称作蚕丝床单,绝大部分是备着丧葬所用。凡有人去世,主客必送一床蚕丝单,没有是不行的,被视为不懂礼节,而死者获得蚕丝单越多越好。有的人家收到的蚕丝单过多,就会保存一部分,留着将来的丧事送礼。苗族每个人都必备一件丝质寿衣。并且,在许多重大的仪式活动中必须要着丝绸服装。比如在苗族重大的鼓藏节期间,鼓社头必须穿丝织鼓社服;大祭典活动时,祭师也必须穿丝质服装等等。
前文曾引述过《苗族古歌·十二个蛋》中,提到蚕和纸的关系:“蛾儿生蚕蛋,蛾儿生了它不抱,让绐谁来抱?蛾儿生蚕蛋,生在构皮纸上,交绐火炕抱。”构皮树即楮皮,是楚国造纸的主要原料和楚纸特征。黔东南苗族民间有《造纸歌》流传,丹寨县苗族民间现在仍有古法造纸工艺传承,其工艺流程与唐代一模一样,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生产的一种传统的皮纸,其颜色和外观很像民间的蚕丝单,质地也很柔韧。这种纸主要的功用在丧葬上。逝者装殓前,先在棺材里铺上很多皮纸,装殓后,把先铺上的皮纸一层层折合在逝者身上,裹得严严实实,棺木里出现空间,需用木炭填实的,也用皮纸将木炭包好。
是什么原因使得没有文字、不需书写的族群将古代的造纸技能一直传承至今呢?我们可以推断,苗族最初的造纸,并非为书写文字,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书写文字,抑或就是蚕丝帛的替代品或新产品。但是在今天,由于市场的丝绸逐渐取代民间的蚕丝单,民间的养蚕也消失了,皮纸真正继承了蚕丝单的遗愿,为逝者引导通向再生的图腾。
在苗族各种工艺的服饰图案中,蝴蝶是俯拾皆是的,而丹寨县雅灰乡和榕江县高排乡等地的苗族百鸟衣上,大面积地使用丝帛和丝线刺绣,常在中心位置绣着一种奇特造型的动物图案,头是变形的鸟头,身是虫身,有节,周围是飞舞的蝴蝶。不少人解释它为龙。其实那是蚕虫、鸟、蝴蝶的结合:蝴蝶——鸟——蚕虫——一幅图本身就包含了蝴蝶图腾的全部寓意。
蝴蝶图腾是苗族先民对蚕桑这一卵生变态生命形式的崇拜结果,是苗族的生命图腾。而蝴蝶图腾是丝绸的起源。中国人利用野蚕吐出的丝进行纺织,创造了灿烂的丝绸及文化,美化了古今人类的生活。


图/曾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