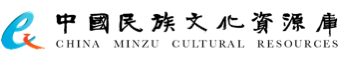
摘要: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关键词:饮食;文化;人类;多样饮食;文化人类;多样
一、饮食与文化
徐新建:围绕人类学视角进行多学科对话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时间我们在《光明日报》也组织了一次关于“口述历史”的对话,因为口语化,很生动,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肯定。这次大家为参加“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研讨会”从各自的远方赶到成都,时间紧、议题广,多有言而未尽之感。所以今天乘此机会再聚一次,组织一个小范围的漫谈,继续讨论“饮食与文化”的关系,希望能在“饮食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下,把话题打开,不求一致,不作定论。最近几天各位的发言都很有意思,互不相同观点之间已展开了热烈争论。现在就请各位发表高论。
王明珂:好,我来做一个开始好了。这个讨论牵涉到文化。这些年对于文化的看法有了变迁:就是把文化当作是“客观存在的符号”。这是一个受到很多检讨的概念。我今天讲的东西正好印证了这个概念。到底文化是什么?比如以四川北川这个地方的饮食来讲,并不是那些客观存在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族群的边界或ethnic marker;我群跟他群的区别,是主观建构的,是人们主观想象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研究的(羌族)黑水河地区,从上游到下游,以羌族地区来讲为赤布舒、再过来是三龙沟、再过来是黑虎。我去问黑虎沟的人,当他们在讲到三龙沟的人时候,他会说那边是“蛮子”。老一辈的人说,那边的人是吃酥油的。吃酥油的现在来看就是藏族,以前没有这样的民族分类就是讲蛮子。可是吃酥油这样的文化(特征)就能区别这两个(民族)吗?不是!你到了三龙沟,就会发现,问他们吃酥油吗?(他们会说)不是,我们哪里会吃酥油?吃酥油的是赤布舒的人。你到了赤布舒,他们那边还是不吃酥油。他们的确不吃酥油,真正吃酥油的是再往上游的黑水人。所以(食物在这)只是一个主观的想象,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项目,能够区分你我。当然这种主观的想象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展演,北川的少数民族认同现在强了,像我讲的荞麦在北川的羌族认同之下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以前荞麦大家都认为是蛮子吃的食物,它现在好不容易从一个被污化的蛮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争取成为羌族了。透过羌族知识分子各种的书写,就把荞麦变成了本民族的谷神,甚至是最有典型(意义)的食物。你在这当中会看到各种展演(performance)。比如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一桌子菜,先上来的是乔凉面,然后会说:各位来宾,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现在桌上的乔凉面是我们北川最有特色的食物。文化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在争论,一方面在界定,一方面在展演,而不是那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
徐新建:你讲的开头是一个大的题目,就是说关于饮食的探讨可能还要回到一个长时期研究的问题:文化是什么?从你这个角度讲,可能有两个层面需要关注:一个是对于文化是什么,在全球化的场景中,中国的本土经验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和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就是说如何参与世界范围里的共识性理论建构。现在我们大家引用的西方的理论比较多。关于文化的定义,早期多以为从西方找到的是结论性真理;后来随着西方学界的自身变化,又慢慢发现,其实对文化的解释并没有定论。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或一种反思:在研究中国的族群和族群文化的时候,能否对解释像“文化”这样的一些基础性关键词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我想这应当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此外,我在昨天的会上评议台湾学者的发言。我把他们的观点概括为:把从基本食物到美食的演变,看作是文化产生的标志;其不是族群区分的标志,而是人类、动物或生物界之间出现区分的标志。由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的饮食传统能够提供何种新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从食品、食具到烹饪方式,再到一些进食方式,都表明文化的产生和进步。这样的看法能否经得起推敲?其引出的结论有没有普遍意义?我觉得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局部的个案性的研讨,中国的远古事例能不能为一种更基础的普遍理论研究提供独到的支持?饮食文化是区域性的还是普遍性的?需要再深入讨论。
王明珂:我想坚持的观点是:客观的饮食并不是一个可以分别出我群与他群的标志。
徐杰舜:我觉得饮食还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边界。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边界来讲,中餐与西餐就划分了两个明显的族群。
王明珂:老徐(徐杰舜),说实在你刚才讲的那两个命题我都不太同意。我们可以来深入讨论一下。首先,中餐与西餐之间是截然两种差别。中国人与西方社会中间根本就没有边界,所以这个例子应该放到美国的社会去。一个美国的华裔是不是在用中餐与西餐来表现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不同呢,这不一定。这就要看你的族群认同和有没有这样的认同危机。在我认识的很多的美国家庭中,他们都喜欢在周末上中餐馆,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忌讳都没有,不会觉得这是别的民族的食物。
徐杰舜:但是王先生,除了中餐西餐可以划分不同族群外,我还想补充一下“侗不离酸”的问题,这的确是一种独特的饮食体系。王先生认为饮食是主观构建的一种体系,但是饮食作为侗族文化的边界,就是(侗家)的所有东西全部酸化,这不只是偶然的一种特点。傣族也是有酸的,海南岛的黎族也吃酸,但从侗族的文化体系来讲,其所有的东西全部酸化,而这种酸又渗透到其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人生礼仪到小孩子的一些仪式通常与酸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我说的文化的边界,在饮食这方面是非常鲜明的。别的人,一般情况下很难接受。但是你讲到的文化的变迁我完全赞同,文化会不断的变迁,包括我们现在吃麦当劳也是一种变迁。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每天、每餐吃麦当劳。
彭兆荣:这是一个语境的问题。我倾向于综合二位的观点。王先生认为食物作为一种物品不足以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志,而徐先生认为可以作为文化边界。我倒不是来和稀泥,我认为食物在有条件的情景之中是可以作为族群认同的一种符号的。其实面包,中国人也吃西方人也吃,但是特殊的context能够使一个具体的物产生特殊的identity。当然,如果排除这样的因素,仅仅用一个食物符号来作为一种族群认同的话或许会有失空泛之感。
邓启耀: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的和神圣的、象征的和现实的食物的区别。同样一种东西,平常吃的和祭祖祭神的时候不是一回事。一个人群或一个地区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因素是很复杂的:宗教的、信仰的、经济的、口味的。本来的没有的现在有了而且上瘾很厉害,像四川的辣椒之类,也应该做行为的和心理的分析。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嗜好,没有那么多深刻的东西。
徐杰舜:所以我想把它归纳一下。饮食能不能作为文化的边界很重要的是要看文化的整体性。如果这个东西在其文化中能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成为一个文化独特的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边界。但是文化是有互动性的,我们天天吃麦当劳也好,天天吃辣椒也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边界是模糊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文化的变迁也可能造成一些变化。我觉得彭兄讲的很有道理,要看在什么情形下来确认食物是否可以作为文化的边界。
二、操弄或想象
王明珂: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食物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以分辨你我的东西,我们反而要自问,为什么经常人类会强调我群与他群的区分的时候,常常主观的将食物当作一个符号。
王秋桂:我是基本上不太赞同明珂说这是“操弄”或是“可想象”的,而成为不能成为识别的符号之一。其实对一个事情的识别由很多种因素组成,食物可以当作其中之一不能单独去用。一个族群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不是单因饮食的原因而已,饮食只是其中之一。你不能说用饮食就能分辨,你不是不能找到跟侗族一样吃辣或吃酸的民族,只以这个来作是绝对不够的。另外我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看个词语,现在大陆已经滥用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了。你再把它弄进去,又要从中间找理论。因为我们用名词,一个名词用出来,你懂,我懂,他懂,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在讲什么。我们现在讲文化,鞋文化、住文化,什么都是文化,到底这里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我是建议我们能不用文化的时候,就不用文化,要用就要讲清楚你的文化是什么!你的文化也许就不是我的文化,你的信仰是我的迷信,这是理不清的。你要把不清楚的东西用来交流,这谁也不懂了,这比后现代还要后现代。
徐新建:当然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区分。我那天在做评议的时候借题发挥,意思是我们现在坐而论道。这个坐而论道不是饮食行为,而是饮食行为所伴生或后续的言说。其意义在哪里呢?比如说有的族群往往并不存在事实上的边界,但是人类学家在理解和阐释的时候见到和使用了“边界”。这是一种学术行为及其产物。学术的行为怎样介入到这样一个层面中?这让人联想到族群理论的不同说法,比如“根基论”和“建构论”。我在研究的层面发现,在民众中,饮食事象并不总是如人类学者所说的有那么细致严格的区分,而只是一些繁杂的经验性样态,其中往往还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如中国餐饮中所谓的“八大菜系”也是如此。在事实的层面指出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很困难的。在这点上或许我们应该不谈抽象的“文化”而谈具体的“食品”。比如什么叫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是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其实关于“食物”的概念还是值得再界定的。就像刚才启耀也讲了,作为“祭品的食物”与“平常的食品”的区别。学者的研究需要一个梳理,就是人类学或其他什么学应该对食物的研究系统化。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可能把日常的经验性的东西搞复杂,学术在某种意义上会制造生活的负担;另外就是可以把这样的讨论参与到其他领域来展开,比如就是族群理论。族群理论现在在大陆很热,大家都在界定族群跟民族什么关系、跟种族和国家什么关系。如果把饮食行为放进来,有可能会挑战一些现在的描述。
所以我觉得在理论上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建议,把食物看成一种语言。我们应该像语言学一样把它看成一些词汇和语法。我现在特别注重文学人类学的文献研究和文本分析。我们现在对食物有没有做这样分析的可能性?我想应该是有的。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食物能不能成为边界?边界是不是可以改变的?其实改变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文化在空间里成为边界,有时候是因为人群和物种的固定。中国人过去没有吃麦当劳是由于有一个时间差而没机会接受;但事实证明,麦当劳作为一个食物品种是可以被人类其他族群接受的。这些族群里其中当然包括华人。这样自然就会出现麦当劳与饺子的竞争。此外,可口可乐作为一种饮料,为什么对中国传统的茶饮构成威胁?这里面又有一种强大的商品宣传原因:在现代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出现了由商人制造并操控的人造口感。也就是说,西方商人制造的可乐口感正在逐渐威胁中国的茶。至少威胁了中国的茶甚至酒。比如你看,如今在中国人的筵席上,可乐也可以用来碰杯了。在此,我想应该追问的问题是:文化的边界在食品上存在的原因是固定的还是因人而异的?或者说任何现存的边界实际上不过是暂时的替代品?
三、食物与边界
邓启耀:我觉得,食物是界定边界的一种参考因素。像王老师所说,断定一个族群,服饰、语言、食物都是其中的一种(文化表象),食物是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种?族群的边界是很模糊的、互相交融的,在这种情况下,判定边界就需要多种因素的参考(徐杰舜:应该还是有相对边界的),应该避免用边界这个词,很多问题一想说清楚反而说不清楚了。
王明珂: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中国食物与西方食物有一个认同上的边界的话。我在某一种认同毫无问题的时候,我要吃什么食物,爱吃什么吃什么,这那会跟我的认同有关系吗?只有到了认同非常紧张的时候,该吃什么东西,该穿什么衣服就变得很重要了。民族考古学家纪恩·哈特的一篇很简单的论文让考古学界震动。他看到非洲的某个族群,坚守他的服饰传统是边远地区的人,而核心地区爱怎样就怎样。核心没有认同危机,边缘的地方有认同危机的时候反而要去强调他的传统,使用传统来作为一种区分你我的边界。这就让考古学家去思考,他们以前老是用一种相似性(similarity)来作为考古文化的核心,考古学界正在放弃受到这样的影响,尝试用客观的文化特征去建立关于核心与边界的认知。
彭兆荣:我觉得毫无疑问,人,不管是我群与他群还是我和他,如果仅仅是我是无法定义我的。我要定义我自己必须建立一个参照,所以我群和他群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会人为的找一个东西来建构边界,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当作一个边界来区分我群与他群。但是食物是不是可以超越边界,有没有超越边界的案例?我觉得是有的,那种超越边界的、全人类的母体,比如说:替罪羊。羊,作为食物的祭品,好像在文学研究中都有一个母体,在很多场合,替罪羊可能只是一头羊,但是作为替罪羊,它反映了全人类普遍的需要。用一个食物或祭品来面对它将要面对的那种神,用一个东西来转化内心的罪过感和自己内心的焦虑感。在这种意义上,替罪羊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族群边界,具有更大的人类性。尽管可能在不同的族群可能使用不同的祭品:鸡、牛、羊,事实上它的母体是一致的,它表现了人与神,人与内心在对话中的一种将罪过或过失转化为食品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可能作为超越族群的母题出现。
徐杰舜:我们应该关注到饮食的功能层面。当饮食仅仅是为了保肚皮的时候,比如原始时代要么吃动物要么吃采集来的东西。当饮食上升到文化的时候,我们在皇城老妈那里已经不仅仅是吃火锅了,一系列的细节,小到牙签的盒子都是文化的表现,体现了皇城老妈的文化。
王明珂:兆荣兄提了一个很好的题,将我们引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应该来延续这个主题:scarified food。作为牺牲的食物的文化意义,李亦园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我们应该延续这样一个讨论(王秋桂: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谈另外一个问题)。
徐杰舜:我接着讲完。秋桂先生讲不要用“文化”,但是吃的东西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温饱的时候,就开始上升到精神的东西了。所以在某种语境下,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边界的元素,但不是唯一的。
徐新建:今天讨论有几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辣椒,我觉得辣椒这个话题绝对要挑战川菜。很多人在不知道“作物传播史”的时候,他们以为四川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辣文化,而且还在不断地论证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材料,不知道文化的传播史,所以现在很麻烦。第一要解释,如果是气候与地缘的因素吃辣椒,辣椒没有传入之前这里的人吃什么东西?今天的讨论里,有一个学者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有些早期的替代品:花椒、胡椒。但是辣椒为什么会取代,因为它产量大、经济,所以就取代了。花椒和胡椒比较单一,辣椒综合了他们的功能,这是一种解释。这样的解释里面有很多麻烦,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各地移民迁到巴蜀之前,这块地方的人,比如三星堆的人,他们吃什么?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饮食文化讨论还很薄,包括“八大菜系”也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广延的、有历史厚度的中国饮食文化传统。所以讲“三辣”: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应该以“辣椒”这个原材料为根本命题,首先解释辣椒由美洲进入中国以前的中国饮食文化。今天作为四川人的族群主体的文化不能解释三星堆,不能解释湖广添四川以前的这块土地上的情况。
王明珂:那天我在王铭铭的课堂讲座上,和学生一起讨论起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但我们大家都共同承认有这样一个现象。你如果相信这一类的说法都是真实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人口就像玩大风车一样的,山东人认为自己是山西来的,湖北人认为自己是江西来的等等,都不是本地人。这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其中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你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湖广填四川,然后到资料里面找那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这当然是可以找到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现在四川几乎80的人都说自己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部分省份的人都说自己是外地来的。而且它虚构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不要忘了,每一个家族讲起来不是说湖广填四川,而是说湖广麻城孝感,那个小乡来的,山西是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个小地方。
四、夸耀和模仿
彭兆荣:毫无疑问,地缘性的食品是有的,在某一个地方,食品具有某种特征。但是我觉得仅仅讨论地缘食品或地缘人群对食品的认同是不够的。这其中或许忽略了地缘食品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通常我们讨论得最多,老百姓也知道的就是“生态”了。某地比较潮湿吃辣去寒,老百姓都会讲。我觉得有两种理论可以让我们借助去讨论,为什么在这个地缘上有这样的地缘食品。一个是人类学的理论:新进化论。萨林斯实际上是新进化论者,他的观点与我们完全相反,我们今天认为在城市里面的人是最幸福的,生活过得最好的。萨林斯恰恰相反,他认为在自然状态生活的那些人生活更好些。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大自然给他提供的更大的能量。而在都市里,人的生活空间被污染。新进化论者试图通过人与自然以及其所能够提供的一群人的能量来说明自然与人群的关系,所以食品在这个理论下是可以有一个解释的。还有一个解释,我们借助于农学家的观点。农学家的解释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人群是传统的农业伦理的话,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土地捆绑”的农业文明。人群失去了土地便等于失去了家园,被置于无家可归的境地,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传统的农业人群中,具有“土地捆绑”关系的情况下,土地的使用以及水土的保养,北方旱作是保山,南方水田是保肥。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人们与土地建立的亲密关系以及亲密关系产生出来的特产:北方的粟与麦,南方的稻作文化。这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地缘食品如何发生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生态问题。
王秋桂:你可以在上海穿一个傣族的服装,人们会觉得很奇怪。而你在上海开设一个有民族特色的饮食点,人人都可以去吃的。饮食与服饰、居住环境不一样,饮食是不容易发生冲突的。饮食的游离性很高,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所以明珂拒绝把这个当成文化认同的标志,我说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但是我们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讲话往往没有交集点,没有焦点便是各人讲各人的事情,这样讲起来是没有用的。
王明珂:我刚才问新建关于四川人吃辣的问题,到底在文献上,四川人被强调爱吃辣椒在文献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就是考虑它的文本什么时候出现,文本是用什么样的文类来传递,谁写的,他怎样把他当作一个社会记忆来推广,到最后才会接上所谓成瘾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化与人的生物性的问题。其实今天大家忽略了在某种情况下,人是生物性的。其实社会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要是认为成瘾是完全的社会性或生物性的反映恐怕是不完全的。这在法国的社会学中早就提了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整个社会环境里面追问。
徐新建:其实我们慢慢把很多问题辨析了。明珂的研究逐渐走向方法论———我感觉你要对人类学进行一个汇总,可能会出现一些理论上的建构。包括明珂提到的文本的出现、文类的影响、心性———心性在你这里特别有一个特点。心性代表族群边界的,而且这个心性跟地缘也有关系,它不是一个普及性的。这是这个阶段要讨论的。但是包括你用的很多比如“攀附”这样的一些词语来解释的现象,从饮食这个角度讲是很奇特。大家可以关注的话,就是说在这些饮食的夸耀式的表达或者表征这样一个过程中,很奇怪大家更多强调的是差异,而且人们总是要有意淡化“相同”,而且有意抹去这个历史事实。这样,一个圈子有一个的基本认同物,比如“麦食”和“米食”。其实在“米食”内部,也有我们一般说的粘米、糯米之分,但通常不被强调。所以在谈所谓“稻作”或“米食”的时候,往往就被忽略了。
与此相关的是,人们通常更愿意讲“菜”。可能在表征上讲,菜比较鲜明。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在两个同时存在现象里突出大范围的差异性呢?在这方面,一些族群边界论者谈过一点。比如上次谈到生态资源的争夺和保护,那么在饮食文化里,这种夸耀和强调差异性,可能有一种功能。其成因何在呢?
王明珂:要造成区分。其实夸耀跟模仿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有一方要模仿另一方人,另一方人就要夸耀以造成自身。举一个例子,这跟今天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发言相关。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讲的都是饮食文化,Jack Goody讲的是明清时候,士大夫阶层怎样通过“文类”的书写来举了饮食文化的精致化的例子。其实,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忽略了在中国的士大夫来讲,他们也在夸耀“堆造美食”,可是从宋代以来的传统来看的话,不是讲忽略了另一种文类。有一本明清笔记小说大观,从里面分析,写美食的文类很少,另一种文类是非常多的,是在教你怎么品评砚、笔———当时的古董什么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宋代以来的商人阶级兴起以后,商人地位是低的,他要去模仿士大夫的这种生活,追求士大夫的风尚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这就是我讲的模仿。对士大夫来讲,一个“反模仿”就是“夸耀”。夸耀一种品味———把这类东西弄得非常模糊,我敢说这就是Jack Goody不对的地方:这个“品味”绝对不是食物的品味,士大夫怎么跟商人去比食物的品味呢?只是在玩弄这种“文人品味”。就是这个花瓶放在你家里,没品味;放在我家里就有品味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放。这个山石该怎么去整他,看你们就弄得没品味,我们就弄得有品味。就是用“品味”来表现的阶级:士大夫跟商人阶级的区分。如果你去看布迪厄的distinction在西方社会,是用植物来作品味的区分。而在中国宋代以来,是用文人的雅好来区分的。我讲的就是一个“夸耀”和模仿。最后,Jack Goody在清代以后,两个文化有点合流,说文人跟着商人追求饮食什么的。其实宋代以来的“士大夫”跟清代的“士绅”概念是不一样的。
徐新建:顺着你的思路,我获得的启发是:我们如果从人类学或者其他什么学对植物进行“分类”,就是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或许分成三大类型,以帮助我们的讨论:一是“生物性的食物”,二是“宗教性的食物”,三是“社会性的食物”。“社会性的食物”跟前两者是有区别的。在“社会性的食物”类型里,夸耀也好、强调差别、边界也好,里面有一个争夺。而强调“生物性食物”的时候,往往把“争夺”看成生存性资源——草地、耕地的争夺。在城市里面,满足“果腹”功能以后,就要“争夺”社会资源。
彭兆荣:刚才明珂兄讲的又把我们提高到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文人中间“品味”并不是我们可以吃和消化的一个东西;它上升到某个东西。这就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食物作为想象的符号,所附着的社会价值。我今天评解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海参的文章。海参是一种海洋生物食品。可是海参之所以被中国人所接纳,而没有被日本人接纳,而日本人特别接纳金鱼,中国人没有接纳金鱼。在作为生物的食物中间,附加上了社会价值的想象性。所以你看“参”是中国食品的一个很高的价值。那么把这样一个想象的社会价值放在海参的符号上,就赋予了一种特别的价值,跟其他的鱼就不一样了。这种想象社会的社会价值附着在这上面以后,形成了一种社会价值的流动。尤其是闽粤两省的华人,他们所建构起来的海参的想象符号,对中国人具有巨大的穿透力。我们从这个例子说明在食物上可以附加进去一个特定的、想象性的社会价值。而事实上,要对海参作分析的话,是不是具有中国人给予的这么高的价值呢?显然没有。我去德国时候,曾带一个很好的海参给德国朋友。他说我们不信这种东西,只有你们中国人信。我们辛辛苦苦花钱买好参,他们当作不屑一顾的东西。这说明人可以通过一个符号附加上社会价值。这个或许是王明珂先生说的文人为什么要品味竹、陶瓷,为什么附加上品味给这种吃的东西呢?事实上具有这种社会符号的想象性。
梁枢(《光明日报》编辑):有一种可能性。所谓生活水平越高,离用饮食来认定的标准越远。放到大尺度讲,21世纪讲不清楚呢,放到22世纪,整个人都发生变化,那吃什么?还在争论饮食搞族群认同是什么意义?现在他们的整个逻辑是下来了。王先生说夸耀是为了区分。区分我想问是为了什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瓜分?彭兆荣用海参来说,这里头是有区别,海参和四川的“辣”、侗族的“酸”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四川的麻辣和“酸”不是资源,不是一个炫耀的东西。
徐新建:这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涉及人类学跟其他学科对话的问题。关于炫耀和强调差异。在强调差异的同时,有一种比附,就是说有一种内在的竞争。通过“比”,可以比出高低、优雅、高下,绝不是平等的比。不然没有意思。比高下、优劣之中有一个共同特点,“我群”跟“他群”比的时候一定是夸耀我自己。比如以“辣”的含义讲,真是把汉语用足了,三个字:“不”、“怕”、“辣”。这里面首先有一种区分:“怕的人”;然后再分,“不怕”的人还要分成3个等级:“辣不怕”,是不够的,然后“不怕辣”就比较有英雄气概了;最高等级是“怕不辣”———“不辣我才怕”呢。所以(社会)资源还要再分,分成三种同样用汉字来构造的等级。这种划分的结果就是选出一个文化优越性。这个文化优越性从民间讲有一种满足感。从另外一方面有一个东西再争夺。现在民间的食品市场化。比如说我从贵州来,发现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说自己是最高等级,都说我们是才“怕不辣”。在贵州,他们说四川是“不怕辣”,湖南是“辣不怕”,我们是“怕不辣”。贵州推出一个产品:老干妈。“老干妈”这个油辣椒产出两个影响,因为其中附带着资源,社会资源转化成经济资源。
我读福山的书,他讨论历史的终结,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强调人类在追求价值最高层面上是自我实现,亦即“被承认”。这实际上就是夸耀,夸耀自己是最纯粹的人、最优等的人。这样的目标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达到,比如认同的需求。这种认同的需求不是一般的“我”跟“你”是什么,是“我”跟“你”有什么不同。这种认同就是“我比你更优越”。用辣椒讲,后面隐藏着更多的没有发现的问题,老百姓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得到一种心理满足。
五、现实和表演
王明珂:大家讨论到这里,有一点蛮有意思。一种是“现实(practice),一种是“表演”(performance)。在现实的环境里,大家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表演当中,却出现了意志。我有意要造成我是领导,要不然就吃非常高档的美食。
梁枢:但是价值体系恰恰是暂时性的。
邓启耀:不变的里面还要加一些历史性的因素,原来说的地理因素肯定也是因素之一,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些就包含了一种传统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比如在某些场合要做某些仪式,在某个仪式中用这些饮食。也许根本不好处理。特别是用来做样子的有某种特定的含义。有平时吃的,当然也有是禁食的,平时不能吃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饮食都有变和不变这一点。
徐杰舜:我想补充一下:我们现在所讲的食物,对人的最愉悦的就是口感。有的喜欢甜的,有的喜欢辣的,有的喜欢咸的、淡的。这是自然过程中的一个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在四川现在是以“辣”为符号;在辣以前可能是以其他的为符号。这是肯定的,还没有深入研究下去。也可能是花椒之类的东西。所以四川确实花椒还留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是吃酸,酸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吃的是面食,也是要和醋才能有助于消化。为什么江浙一带喜欢甜呢———炒菜都要放糖呢?因为他的口感是自然过程中的最实用的一种选择。这样东西形成了,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边界?他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就难受。第二点,除了选择之外,还有一种适当的追求。现在的社会,文化在互动、传播、变迁,现在的东西,很多讲吃辣,吃辣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还到国外去了。
彭兆荣:我们刚才谈了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全人类把食物作为一种共同的———比如替罪羊的符号,可以超越人群的一种可能性。这我们没有谈,显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层面,就是人类共同在食物上选择某个母题的。第二种情况讲的是地缘性。我们讲所谓八大菜系,地缘作为符号的一个特点。假如有边界的话,地缘作为一个边界,族群也是一个边界。我想到作为个人的生命体来说,还存在一个更低的、更低层的、习惯性的家族的口感。我自己都有体验:外面的五星级吃完以后,回去吃妈妈的菜是最好的,不仅仅是对家族的一个忠诚,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可能太大。是不是有存在着一种家族的口感存在呢?我个人体验,细腻一点是有的。这种口味的存在是不是说家族、家庭可以作为一条边界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可以有从大到小的一个体系。
王秋桂:你讲家人,是更小的一个,是个人的东西。我想这种问题,还是大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最后你怎么把它抽成一个东西来?川菜是辣的,闽菜多汤,到现在,以台湾传统讲,我找不到一家道地的川菜,包括台菜也没有一家道地的台菜。反正已经杂成一起了。这里也一样,我们吃了几家,到底哪家是道地的川菜?一两个菜也许是,整个下来,哪里有什么川菜?所以这种东西,可以消失得很快,八大菜系已经混得一塌糊涂了。在台湾最明显,在任何餐厅都不可能吃到单一一个菜系的菜。不可能有这种事情。饮食是很容易可以游离出去的。可以从个人到家庭、社会,这个地区的族群。用这个来分辨,像明珂说的,很难确定说这个可以代表什么。到最后都归结到个人了。我一个朋友到台湾,说要辣,我切了一小片辣椒给他,他吃了一片就不敢吃了。他说是“怕不辣”的。台湾的小辣椒很辣,他们没有办法再开嘴。
那种辣椒是意大利的辣椒。所以,明珂在他的书里面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所谓的族群的概念,是一个进行的观念,羌族就是那样。中国的每一个族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明珂的书把“民族”都打破了。这每一个概念———民族都有各种不同的东西,我们怎样考虑?从社会的、记忆的、文化的角度考虑,角度很多。所以我们谈,要目的明确,大家都在这个题目谈。谈完了可以弄一个东西,要不然五光十色。
六、比较和记忆
徐新建:我也觉得有两个话题,不谈可能会漏掉。一个是王先生的很好的话题:区分和比较。一个是明珂的,我们谈到区分、记忆。
梁枢:我先插一句: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有两个东西不变,就是刚才邓启耀说的。一个是必须得吃,不管吃什么都得吃。一个是刚才你们说的,从王先生那里,说夸耀是为了区分,区分是为了分割社会资源。好像区分是永恒的。
徐新建:那不一定,看你怎么看。我们还可以谈谈关于区分的评价和解读。关于“区分”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种无意识的强调和别的忽略。刚才王先生讲川菜,我觉得都市的菜系在混淆,完全是大杂烩。但是到周边去,去农家乐等地方,那些老百姓讲得出多少“餐馆”、“厨师”或“菜系”啊?他知道的就是父辈的传承;用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原材料:后山养的猪,前院种的菜,也不知道什么“转基因”。这些人在存留和保护的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需要关注现在正在被忽略的“社会阶层”。如不注意,许多重要的东西将会流失,这是其一。其二,这次会上有人提到“七十而吃肉”,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年龄的阶层。这有几层含义:一是生物学的含义,不同年龄段的食品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食品对不同的年龄段意味着的功能都不一样。这是......
彭兆荣:譬如说“伟哥”是拿给中老年男人吃的。
徐新建:现在还没有提到性别的问题。所以我们区分的边界是不是过度地强调族群、国家、地缘,而忽略其他的同样存在的边界和区分?这倒是要提出考虑的。另一个,刚才王先生提到的,在文化的基本要素上讲“衣食住行”或“生老病死”,包括建筑那些,里面有一个关于“食品”这个符号跟其他符号的差别。比如说,如果其他相对稳定的话,食品是流动的。我们可能会把“衣食住行”当作固定特质的来谈———“中华民族的衣食住行”。但是谈“食”就危险。因为“食”可能作为可以传播的,可以影响、借鉴、模仿的,跟“衣”“住”不一样。这里面还可以讨论。因为是暂时的。为什么“食”可以流动,其他东西相对稳定?我觉得原因可能是社会学上的。可能“衣食住行”在根本上都是流动的,只不过在表现上有的流动性强,有的流动性弱。这个符号性本身的问题还提到了“礼”。比如服装可以流动,你既不可随心所欲,也无法任意阻挡。而且从都市到农村,从汉族到其他民族,这个服装在流动,所谓“流动”就是边界的消解。
与此相似,口味的流动也是如此;建筑亦然。你看许多被视为珍品的老建筑哪里还容易见到?人的住房已经很少有独特性了。旅馆是标准化的,学校是标准化的,哪里还有什么特点?川大保留了两栋以前设计的老房子,被骂不实用———大屋顶。所以这里面的问题———接着王先生的话题———是不是这些文化要素都是同样的,或者不同,为什么?那么食物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族群、地区里面扮演的角色可能也会不同。
七、吃什么和怎样吃
彭兆荣: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些德国的学者到中国,中国当时很穷,请人到家里来,供了一大桌菜,夹菜夹菜,结果德国人回去以后说中国文化在食物中间具有巨大的压迫感,对他不尊敬。
徐新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我们刚才谈的是“吃什么”,现在你谈的是“怎样吃”。饮食文化还得再分类。一是食物跟人的关系。那么“食”是一个层面,“吃”是行为,都有一个“吃”。所有的食物只有通过“吃”才能成为食物,人类的食物。所以刚才谈“吃什么”的时候,选择也好区分也好,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个层面。现在谈“怎样吃”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你刚才讲这种劝酒,作为一个文化区分和文化差度。你说它“强制”,我说他根本没有读懂。因为这种文化为什么会敬酒?“不醉不归”,你这种知识分子觉得醉酒是痛苦,“酒后失性”、“酒后失言”是你的生活的压抑的问题,而你觉得西装革履的醉倒在路边很不像话。你这种文化状态对于他那种文化状态的时候,你就要拒绝他那种饮酒。你觉得他强迫你,事实上你根本在这个文化里面。反过来,你是外人,在他们的文化圈子里面,你看他们是不是强迫,不是强迫。你不接受他的敬酒,他觉得你太小气太不对我好了。酒是可以自己喝的,为什么一定要人敬?就是说我的酒在这里,要怎么样?吃进去啊,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敬酒的时候要唱歌,结果是大家要忘记自己的差别和区分。我们强调区分是礼,而酒带来的是忘礼的分别。所以你说的那个“怎样吃”恰恰是两种不同的礼。你说的那个德国人真的是一种误读,他把这当作一种野蛮了。
彭兆荣:也不能这样说。你完全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评价人家。
徐杰舜:对对对。首先是中国误读了他。
彭兆荣:这个文化的相互交流不够,所以造成了不理解。他其实是知道你的慷慨的,倒是他的认识价值不同,在他的习惯里面他不喜欢人家做一种。你说他是误读你。本身他是到你中间来,你把这个错推到他身上去,这是不公平的。他可以说他不了解你的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你也不了解他。在这个意义上,双方是平等的。他有权利说你强迫了他,你也有权利说我对你这么好,你还好心当作驴肝肺。其实这个意义上双方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哪一个对多一点。我想我用两句话来总结,To eat or not,that is out of question吃还是不吃是毫无疑问的。How to eat,that is the question怎么吃这是个问题。
王明珂:我最后再抛出一个问题,大家回去考虑一下。我刚才在思考,在生物多样性的环境里,我们讲一个生态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鸟在这里,结果它们发展出来后,有的脚长有的嘴短。我们知道在生物上这可以让它们吃到不同的植物,对不对?同时这种区分可以让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是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人类的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样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源的。我们不仅是利用而已,我们还加工和改造,然后我们这样造成社会的区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与生物性、生态和文化有关。这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好吃的拼命的膨胀,不好吃的就消失了,找不到了。那长腿的鸟和长嘴的鸟就没有办法了,形成了一种模式的鸟。这样一旦出现了问题,全部灭绝。
徐新建: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到了。到此结束,以后再谈。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资料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