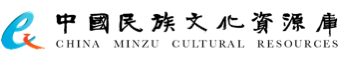
我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不离林先生左右,所以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已不是写得动大块文章的时候了,只能凭记忆所及,平铺直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我愿意用这些情况,折射出林先生教学和研究生涯中的一些闪光之处。
我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较林先生晚了将近10年。开始时我读的是新闻系,那是埃德加·斯诺任教的地方,后来才转到社会学系。当时林先生还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我虽有幸拜读过林先生的一些著作,却未曾谋面,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机缘终于悄然而至。1942年夏,成都燕京大学请林先生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他从昆明到成都赴任,要经过重庆。我则因前一年考上研究生后,刚读了半年就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遂逃往重庆。其时正逢暑假,我来到重庆吴文藻先生家中讨教今后的选题和调查选点问题,就在七星岗吴先生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先生。那时的他32岁,英姿勃发,在学术界已有名气,还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头衔,正是年轻学子们的“心中偶像”。
不久,林先生到成都赴任。我则衔吴先生之命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学院,目的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新疆少数民族资料,以便将来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政治投机,表面招揽人才,实则暗地严加防范。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受到限制,难以开展。1944年8月,我更被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投进监狱,备受煎熬达数月之久,直到1944年12月才得以出狱。
盛世才抓我全无理由,所以我出狱后不愿再待在新疆,于是就罢教离职而去,回到成都燕大。从此,我就一边做林先生的助教,一边读研究生。1943年至1945年期间,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合作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并建起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凉山彝家》的考察工作即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944年夏,林先生调查康北藏族。1945年夏,他又调查四土嘉戎,我以助教兼研究生的身份参加了调查,这是我首次接触四川藏族调查。在与林先生朝夕相处的两个半月里,我对林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先生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还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在准备前往嘉戎地区进行调查时,林先生的第一个孩子宗锦刚出世,而且在生病。同在成都燕大执教的饶先生(林先生夫人)希望他暑假能够留在成都,但林先生认为暑假时间长,有两个多月,可以从事田野工作,坚持要出行。嘉戎藏族聚居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既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也有冲积而成的台地和河谷平原。我们在这里考察,经常要跋山涉水,但是林先生工作起来非常投入,在崎岖的山路上也走得很快。为了行动方便,我们随身只带着少量的粮食和简单的日用品。一个脸盆,除了洗脸、洗衣服,还要煮面条、盛面。
不只是生活上的艰苦,我们还要随时面对各种危险。当时嘉戎地区很多人种植鸦片,为了防止川甘地区的袍哥组织(晚清四川地区的民间帮会组织)向那里运送武器,向外输出鸦片,所有人员出入嘉戎都要接受军队检查。林先生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还有四川省政府开具的研究证明,所以路上还算顺利。嘉戎土司本身就是袍哥,结交的外人也多为袍哥。为了调查方便,林先生每到一地都要先去拜访袍哥。在杂谷脑,我们拜访了那里的“舵把子”王某,他将我们介绍给土司索观瀛。索土司其人交游很广,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林先生在人事疏通方面也有些办法,记得当地有一位汉族土郎中,我们和他交情很好,临离开时把剩下的药送他很多,他很高兴。
危险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在进入山区后,我们要通过一片没有道路的山林,请了一位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和工人在前面走得很快,很快就不见了身影。在一个悬崖附近,我一脚踩在松软的地方,径直就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暂时停住。林先生想办法把我拽了上来。这时天渐渐黑了,我们只好在大树底下等向导。树林中刚下过雨,我们的衣服全都湿了。林先生凭借多年田野工作的经验,说是要生火防御野兽。我们把笔记本、手帕等身上之物都拿来点火,直到把火柴划剩下两根时,还是因为潮湿没点着火。我们不敢再用火柴了,只能在黑暗中等待。夜半时分,我困得睡过去,林先生又唤我起来,说不能睡,否则会得大病。我被唤醒数次,又怕兽蛇的侵扰,这样勉强熬到天亮,才等来向导和工人。从嘉戎地区返回时,我们雇了两匹马。有一次,骑在马上的林先生不小心被树枝卡住,而马因为受惊却向前疯跑,一下子将林先生摔了下来,可他的脚还卡在马蹬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身上穿的风雨衣都被刮破了。
在调查中怎样提问,怎样得到更多的材料却又能避开访谈对象不愿回答的问题,这些都很费心思。林先生在这一点上很有技巧。做调查要访问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如藏文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就找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的汉族访谈。在调查嘉戎土司与四周的交往时,我们找到了索观瀛的亲家——黑水头人苏永和。索观瀛的大儿子是个活佛,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嘉戎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活动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林先生撰写的《四土嘉戎》的文稿已经被送到商务印书馆,却因为战乱丢失了,很可惜。
从成都回到北京后,我仍做林先生的助教,毕业后留在系里独立开课。其间我经常征求林先生的意见,可以说,林先生是我独立走上民族学教学和科研岗位的领路人。林先生教书很用功,博闻强记,口才虽不像燕京大学的某些教授那样出色,但掌握的材料很丰富,传授的知识很扎实。
林先生在政治上也追求进步。燕大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学生多,二是参加学生运动的多。师生都关心社会现实,倾向进步。在成都时,林先生就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到北京后,饶先生的弟弟饶疏菩是燕大医预科学生,也是地下党员。他就住在林先生家,所以地下组织的许多会议都是在林家举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林先生算是一帆风顺。他很快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学说,并能够在研究中加以运用。燕京大学解放后聘请了一些左派进步教授,林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系也请来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开设了“中国社会史”课程。林先生时常与之接触,并在此期间写出《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由耕耘出版社出版。
1951年,林先生跟随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后,林先生的职务由我代理。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国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大部分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并多半在研究部工作。林先生从西藏回来后,也进了研究部,在此后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林先生都承担起了重任。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师,到了“文革”时也不能幸免。“文革”开始时,林先生还在广西参加四清,奉召返京时一下车,就被戴上高帽子,还被泼了一头墨汁。他在运动中受的冲击较大,精神上负担很重,在很长时间里不吃安眠药就很难入睡。
其实早在“文革”前夕,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色彩就已经很浓厚了。学术界有很多人反对民族学,认为可以用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来研究民族问题,根本不需要民族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由于林先生一直强调民族学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当学科被否定时,对他造成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林先生所在的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也为了避讳,改叫民族志教研室,但林先生对民族学却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就写信给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要求恢复民族学。终于,1983年,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并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的本科生。
林先生为人循规蹈矩,为学踏踏实实,为师诚恳敬业,对周围的人际关系考虑不多,基本上是一副书呆子形象。他晚年对原始社会史的钻研比较深,如提出原始社会分期中的三分法等。这是他在经历多年政治运动后产生出的兴趣,其中不无自我保护性质,但他对现实问题依然很关注。例如,我提出和参与过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宋蜀华提出的民族学与现代化等课题,林先生都积极参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凡是强调应用、结合现实社会发展的,总是令他格外高兴。做过学生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林耀华先生。(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